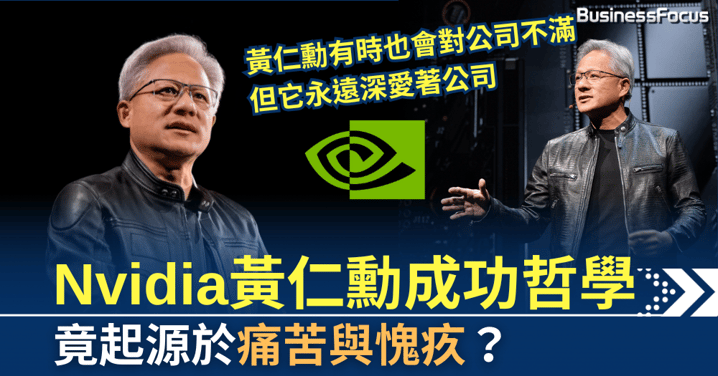
「我祝你痛苦」,黃仁勳的成功哲學,竟起源於痛苦與愧疚
在矽谷,人們習慣歌頌熱情與夢想,但全球AI晶片霸主、Nvidia創辦人黃仁勳的成功,卻植根於一組截然不同的情感:恐懼、焦慮與愧疚。他並非每天快樂地工作,甚至直言偉大來自「痛苦與折磨」。
黃仁勳的成功心法:恐懼、痛苦與偏執如何打造AI帝國
核心驅動力:源自對失敗的恐懼與愧疚
當傳記作家史蒂芬.維特(Stephen Witt)有機會貼身採訪黃仁勳長達六小時後,他發現最令人震驚的,並非黃仁勳的遠見或技術實力,而是其成功的核心驅動引擎,竟是「恐懼」與「愧疚」這兩種看似負面的情緒。
維特在其採訪傳記《The Thinking Machine》中透露:「黃仁勳最讓我驚訝的地方在於,他幾乎可說是被負面情緒所驅動。」他進一步解釋,這份動力具體化為三種心態:對失敗的極度恐懼、在激烈競爭中的多疑偏執,以及對於可能讓員工、股東及合作夥伴失望的強烈愧疚感。
他始終在為可能的失敗做最壞的打算。這份根植於內心的悲觀主義,讓他得以帶領Nvidia度過成立初期的瀕死危機——公司成立三年後幾乎倒閉。他深刻體悟到:「除非你能承受失敗,否則永遠不會嘗試;不嘗試就不會創新,不創新就無法成功。」對黃仁勳而言,恐懼不是絆腳石,而是讓他時刻保持警覺、不斷尋找潛在威脅的警報器。正是這種「隨時可能一敗塗地」的危機感,成為他永不懈怠的根本原因。
擁抱痛苦與折磨:壓力是創新的唯一燃料
世俗普遍認為,理想的工作是快樂的。但黃仁勳對此嗤之以鼻。他曾對應屆畢業生說出那句著名的「祝福」:「我祝你們經歷無數痛苦與折磨(pain and suffering)。」
這段話並非憤世嫉俗,而是他工作哲學的真實寫照。黃仁勳認為,真正有價值、能創造偉大事物的工作,本質上就是艱難的。「你必須承受痛苦、奮鬥掙扎、努力嘗試,挑戰並克服艱難的任務,你才會真正重視自己所做的事。」他相信,舒適與安逸無法帶來非凡成就。當一切進展順利時,他反而會「坐立難安」,認為這代表自己不夠努力,或忽略了潛在的危機。
工作狂的自白:深愛公司,而非工作的每一天
黃仁勳是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每天清晨五、六點起床,便一頭栽進工作,直到深夜闔眼,一週七天,全年無休。他曾說:「沒在工作時我會想著工作,工作時就全心投入。」
然而,這種極致的投入並非源於對工作本身的無限熱愛。他坦承:「我並不總是熱愛自己的工作,也不認為每天都過得很開心。」這句話顛覆了許多人對成功企業家的想像。他進一步解釋:「但快樂並不是美好一天的必要條件。我有時也會對公司不滿,但我永遠深愛著它。」
他的忠誠與熱情,是獻給「Nvidia」,而不是獻給「工作」這項日常活動本身。他的動力來自於確保這家他傾注畢生心血的公司能夠持續生存與卓越,而這種責任感,遠比個人的日常情緒體驗更為重要。
巨頭的工作哲學:黃仁勳、馬斯克與巴菲特的殊途同歸
若將黃仁勳的哲學放在更廣闊的商業領袖光譜中觀察,會發現更有趣的對比。
1.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與黃仁勳同樣是著名工作狂,每週工作時長可達80至120小時,甚至睡在工廠。但馬斯克的驅動力更多來自於一個宏大的、近乎救世主般的未來願景——將人類打造成跨行星物種。他的壓力源於實現這個偉大目標的時間緊迫性,是一種「向未來賽跑」的使命感。
2.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則代表了另一個極端。這位「股神」以其極度清閒的日程表聞名。他每天花大量時間閱讀和思考,避免被日常會議和瑣事干擾。巴菲特的成功來自於耐心、紀律和深思熟慮後的「不作為」。他的動力源於對投資這場智力遊戲的純粹熱愛與好奇心,而非外在的恐懼或壓力。
黃仁勳介於兩者之間,但更偏向壓力驅動。他不像馬斯克那樣時常公開闡述改變人類的宏大敘事,也不像巴菲特那樣享受悠閒的思考。他的哲學更為務實和內斂,聚焦於眼前的競爭與生存,並將對失敗的恐懼轉化為追求極致完美的偏執。
Text by BusinessFocus Editorial
免責聲明:本網頁一切言論並不構成要約、招攬或邀請、誘使、任何不論種類或形式之申述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讀者務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如因相關言論招致損失,概與本公司無涉。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可升可跌。








